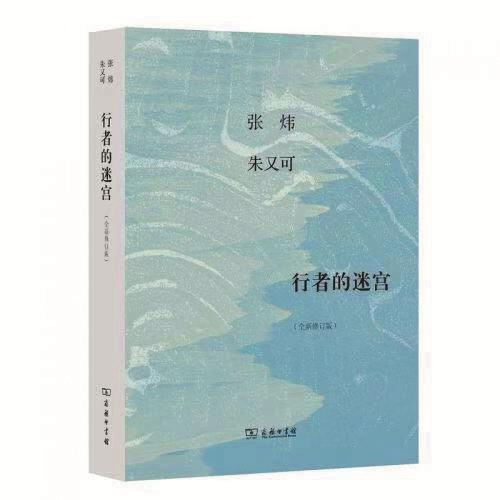
《行者的迷宮》 (全新修訂版) 張煒 朱又可 著 商務印書館 2018年9月
○王威廉
張煒是一個有著極為龐大的精神體量的作家。讀了朱又可先生對他的訪談錄《行者的迷宮》之后,才確切地知道這種強健的精神主體是如何起源的,又是如何在復雜的生活閱歷和人生積累中成形的。行者的迷宮,原來并不是一個隱喻,而是一個實指。盡管張煒在前言里謙遜地將這個標題定位為一個隱喻,但隨著閱讀的深入,在了解他之后,發現他真的是一個行走在大地上的人,他跟大地的關系要比一般的中國作家深得多。他的一生竟然有幾十年都行走在路上,這種行走不是舒適的“自駕游”,就是原始意義上的行走——用腳來丈量土地。他將自己的行走方式比喻成純文學的長篇小說:情節被壓縮,而細節被放大。
迷宮1:土地是人性和文化的共同起源
行走和漫游是張煒從小養成的愛好,對于膠東半島的每一寸土地,他都渴望去踏足并探尋。這最終成了他的生活方式。幾十年來,他一直擴大著游走的范圍,已經不僅僅局限在半島地區,他要在西方和東方、南方和北方,最貧窮和最富裕的地方去觀察,從而使得生活的面積不斷地擴大和敞開。他在行走中多次遇險,好幾次有生命的危險,這讓我對他的寫作有了更多的敬重。
張煒信任土地、親近土地,是因為他相信土地是人性和文化的共同起源。我們這個時代,這種地方性知識一方面在全球化、商業化的侵襲下快速消亡,那種彼此模仿的、千篇一律的同質化現象越來越嚴重。鄉村模仿鄉鎮,縣城模仿城市,小城市模仿大城市,大城市模仿巨型都市……網絡時代把立體的空間變成了相似的平面。另外一方面,我們的出走越來越局限,我們經常看到的是人家想讓我們看到的,我也相信世界仍然有巨大的秘密隱藏在那些山水之中,這便是需要行走去突破和發現的。
因此,張煒不是那種只閱讀小說然后便從中孵化小說的食腐動物,他的寫作是及物的。除了漫游之外,他還注重“野知識”的收集。他大學畢業后,在山東檔案局工作過四五年,這讓他接觸到了主流視野以外的大量資料。我這才完全理解了張煒作品中那股與眾不同的時代氣息。他打通了閱讀和行走、經驗與材料,然后又通過巨大的文學能力把他們統攝在一起。
迷宮2:為了一個“遙遠的自我”而寫作
這種龐大的準備期,自然激發了張煒的創作胃口。他的心底誕生了一個雄心壯志,便是去完成一部關于中國當代的多卷本長篇小說。他也不相信中國人寫不出“史詩性”的超長篇作品,因此他想嘗試。更重要的是,張煒想從一個更長的時段來思考中國當代社會。他的“長河小說”《你在高原》于2010年在作家出版社推出,他寫了二十二年,分三十九卷,歸為十個單元,有四百五十萬字之多。他談到,在這二十二年里,他不斷地修改和調整。這種修改和調整,一方面當然是為了讓作品更加完美,讓語言更加體現時代的特點,但另外一方面,這種修改和調整有被動性的一面。因為中國當代社會一直發生著劇烈的變動,多變的政策對于社會的影響是極為顯著的,三年一小變,五年一大變,這使得長卷式的超長篇小說總是跟社會語境產生著各種各樣的疏離、膠著,就像是漩渦的出現而改變了水面的形象,他必須要從中找到一個更恒常的價值,來穿越這些迷惑耳目的歷史風景。
張煒談到了長篇小說的藝術,尤其推崇空間并置的思維方式。在紙上形成一個龐大而錯落有致的建筑群落,正是長篇小說豐贍的結構之美。他還提到了重復之美,舉《西游記》為例,重復的力量不僅僅是簡單的加法,很多重復看上去是相似的,實際上它們總有一些微妙的不同,因而重復會營造出一種更有力量的美學。其實中國的古典小說,有許多小說都采取重復的結構,比如《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等,這種結構的確有它的好處,可以最大程度地容納現實的人生世相。
超長篇小說的寫作是對生命的可怕損耗,因此精神主體不僅得足夠強壯,還得足夠堅韌。張煒談到他年輕時,身體是很強壯的,可以白天采訪記錄,晚上讀書寫作,基本上不需要睡覺。可是,強壯可以撐個一兩年,但絕對撐不起二十幾年。只有堅韌可以。堅韌不是一種力量,而是一種信仰。他有他的信仰。他說自己是為了一個“遙遠的自我”而寫作,那個“我”在更高處,那個“我”在注視著寫作的自己。這讓寫作變成了宗教般的信仰,從而獲得了生命的堅韌。
迷宮3:第二次選擇帶來的存在主義
因此,張煒特別強調文化產品跟藝術作品是不可以混淆的。作為藝術的文學,在他那里是處于一種完全純粹的狀態,他認為寫作沒必要去遷就讀者,那道更高處的目光意味著生命的完成。我對此是很認同的,只有這樣的寫作才是出自生命本身的誠摯,才是對讀者的最大尊重。讀者在這樣的文字中跋涉,才能獲得深沉的人生哲思。
再堅韌的生命也會有絕望和痛苦。張煒談到自己的絕望和痛苦。雖然他很年輕就獲得了世俗意義上的成功,獲得了文學界的認可,按理說不應該有太多的痛苦,但他在社會轉型的物質時代陷入了價值崩裂的痛苦,因此在那場“人文精神大討論”的思潮中,張煒才像斗士那樣去發表言論。他認識到,道德倫理和文化思想不會總是處于一種進步的狀態,隨著歷史的不同階段,這些精神的事物沒法得到有效地儲存和接力。這跟科技文化不一樣,科學技術不但可以儲存還可以接力發展,因而科技才創造了今天這么發達的物質文明。所以,他不是一個頑固的道德論者,他只是在捍衛自己行走在大地上所生長起來的精神價值。
張煒就此提到一點,我覺得很值得深思:對每個人來說,人生的第二次選擇特別重要,因為第一次選擇是憑著人生的熱情和沖動去做的,但是在絕望之后的第二次選擇實際上對生命意味著更多。這才是你對于生命道路的主動選擇,才能讓你承受起人生的絕望和痛苦。這是帶著傷痕和經驗的存在主義。
迷宮4:深感人文精神的失落
張煒是一個過于復雜的人,他的迷人之處就在于他既像是一個古典精神的繼承者,又像是一個現代精神的踐行者。比如,他對于文化的理解,也是放在一個更寬闊的歷史視野當中。他覺得我們應該上承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提及的“整理國故”的號召,把中國傳統文化中那些有益的部分整理下來,成為我們創建新文明的火種和依靠。于是,他花了很多年,主編了徐福的資料集。他并不滿足,他從中國文化的起源處開始尋找,并把他所處的山東沿海的齊文化作為當代跟古代進行連通的一個文化源流。他認為齊文化有著自由和浪漫,有著活潑的想象力,有著百家爭鳴的包容性,這都深深地影響著他和他的創作。此外,他是極為推崇孔子的。他在《芳心似火——兼論齊文化的恣與累》一書中,考證孔子沒有來到齊文化的腹地,但他同樣贊美儒家,他只是反對將儒家形式化、空洞化,他覺得儒家是一門需要去實踐的學問。比如他深感人文精神的失落,便親自創辦了萬松浦書院,希望以一己之力去改變,盡管他深知這樣的改變是極為渺小的。
這是一次極為漫長的談話,能感覺到張煒一點一滴地將自己的生命歷程抽取出來。我覺得他不是一個特別喜歡講漂亮話的人,但他的言辭中透著巨大的懇切。一開始也許你不太習慣他的說話方式,但是讀著讀著,你就被他的闊大和深邃俘獲了。我在閱讀的過程中,仿佛置身聊天的現場,逐漸沉迷在張煒講述的無數細節當中,我反復回味著一些細節,有些場景在我的腦中栩栩如生,我意識到,我置身在他的生命迷宮中了。也許,他的迷宮和我的迷宮已經在某個地方連接在了一起,我要找到那條隱秘的通道。

